作者:禹yuyu
2025年8月25日2首发:第一会所
字数:12295
写在前面:笔者自觉在写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必须要有优秀的武戏和文戏。
这一章里,笔者自认做到了这两点。
感兴趣的诸君很快就会看到数个全新的【领域】。
祝读得愉快。
第十六章:啸天魔君
诗剑行躺在雪地上。
我与离恨烟在冰冷的雪地中温暖地相拥,休息了一会,享受爱意的余韵。
凛冽的寒风在我们身周呼啸,却丝毫无法侵入那由我们二人体温与爱意共同
构筑的、小小的温暖结界。
她的呼吸平稳而均匀,轻柔地扑洒在我的颈间,带着一丝独属于她的、兰花
般的幽香,和一丝我们二人刚刚才在欢爱之中所留下的、充满生命力的甜腻气息。
离恨烟轻轻抚摸着我的脸,那冰凉的、却又无比柔软的指尖,在我那因为连
场激战而显得有些胡子拉碴的下巴上,缓缓地游走、爱怜。而我则将我的手覆在
她被我开发得无比敏感、手感绝佳的雪峰之上,不轻不重地缓缓揉捏。
这是我们应得的安宁。
然而,这份宁静,却再一次被一道温婉身影给毫不留情地打断了。
冷月师母,不知何时,已如鬼魅般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这已经是不知多少次,她打断我们做爱了。
我心里甚至生出一种不敢说出的奇怪想法。
她……她是不是有偷窥别人欢爱的癖好啊?
不行不行!李邵!你这个畜生!
她可是你师母!
是你在这世上,除了烟儿之外,最亲的家人!
你怎么能用这般龌龊的念头去想她?!
我心中那刚刚才冒出头的、大不敬的念头,瞬间便被一股更加强烈的、足以
将我灵魂都彻底淹没的无边愧疚,给彻底地掐灭了。
「孩儿们,穿好衣服吧,」师母看着我们这副衣衫不整、紧紧纠缠在一起的
尴尬模样,她脸上却没有丝毫的波澜,仿佛早已司空见惯,「为师要带你们,去
那围攻最后一位护法——啸天魔君的战场……」
我和烟儿看着自己那并未完全恢复的身体,都有些迟疑。
我们早已从媚儿口中得知,那啸天魔君乃是七品大圆满高手,而且心智成熟,
远非那头脑简单的血手阎罗和那像雌小鬼一样的娇奴可比。
我俩能有什么用?
难道师母竟忍心,让我们这两个刚刚才在她面前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小
英雄」,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去当炮灰吗?
冷月只是轻轻拉起我们。
她那双保养得宜的手,看似轻柔,却又带着一股我们根本无法抗拒的力量。
我们只好跟着她前行。
没过一会,我们便来到那尸山血海面前。
那是一幅我此生都再也无法忘怀的,充满了无尽的悲壮、惨烈与一丝……荒
唐的景象。
我们脚下是被无尽的鲜血与残肢断臂彻底染成一片触目惊心的妖异暗红色的
万载玄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充满了血腥、焦臭与浓郁魔气的死亡
味道。
数以十计来自各大门派的、本该是意气风发的正道豪杰,以及数百具恶鬼的
残尸,此刻却如同一堆堆最卑贱的破烂垃圾般,横七竖八、不分敌我地倒在那冰
冷的、肮脏的血泊之中。?也正是在我们抵达的这一刻,正好目睹了那足以让任
何人都为之胆寒的一幕。
在前日的会议之中,与秦阁主险些动手的,那来自?泰山派的侯长老,他手
中的拂尘已被鲜血浸透,此刻正须发皆张,拼尽全力地抵挡着那如同山岳般砸下
的巨斧。
然而,只听「咔嚓」两声脆响,他那两条仙风道骨的手臂,竟被势不可挡的
巨斧,连同护体的法宝,一同硬生生地斩断!?」老侯!」?秦天雷的身形立刻
化作一道紫色的雷光,在那位长老即将被后续的斧刃彻底劈成两半的瞬间,将他
那血流如注的残躯,险之又险地从那死亡的阴影之下抢救了出来。?放眼望去,
整个战场之上,「天剑」上官影此刻竟不见了踪影;
而焚天谷那位脾气火爆的火长老,也同样是脸色煞白地盘坐在一旁,显然是
真气耗尽,正在紧急地调息。?整个正道联军,竟已被逼入了即将要彻底崩溃的
绝境!?而造成这一切的,便是那个屹立于尸山血海中央的、如同上古魔神般的
恐怖巨人。?那是一尊高达数十丈、青面獠牙、肌肉虬结的怪物。他那如同熔岩
般的皮肤之上,布满了充满了怨念的黑色魔纹;他的口中,不断地喷吐着足以将
空气都彻底点燃的硫磺气息。?我与烟儿看着眼前这尊已超越我们所有想象的
「法天象地」,我们那颗刚刚才在连番大战之中被淬炼得坚如磐石的道心,不受
控制地剧烈颤抖了起来。?我们竟被吓到了。
我们就呆呆地看着,一些尚有一战之力的武林同道已杀红了眼。
他们像一群野兽,发出一声声嘶吼,向着那被他们死死地围困在战场中央的
庞大目标,疯狂地冲了上去!
然而,所有攻击,在落到他那被如同实质般的黑色护体魔气,所彻底包裹的
身体之上的瞬间,便如同一颗颗投入无边无际、汹涌大海之中的微不足道石子般,
被他那诡异如同无底洞般的魔气吞噬!
而那些,本该是这场「正邪大战」之中的中坚力量——那些来自其他二三流
门派、达到了七品「化境」的宗主们,此刻却都跑去清理战场上的魔教杂兵与都
统。
只有少数几名强者,偶尔出手与那魔头过招,但只是几个回合之后便拉开,
生怕自己受伤。?也正是在这时,师母冷月那清冷的、却又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
平静的声音,在我们耳边缓缓响起。?」不必惊慌。」?」……那是『恨天魔相』,
只不过是个为了追求力量,而亲手毁了自己未来的『残缺领域』罢了。」
这句话让我们冷静下来,又顿时变成了义愤填膺。
「剑行……这该死的魔头……!」
离恨烟的声音嘶哑而愤怒,她那原本清冷的气质,此刻却被一种凌厉的杀意
所取代。
我们本想上前助阵,用我二人那心意相通的合击剑法,去助那些强弩之末的
同道一臂之力,却被冷月师母那只冰凉的手,死死地按住了。
她早已施展秘法,把我们的身形气息彻底隐藏。
「师母?」烟儿那双清澈的眼眸之中充满了不解与一丝焦急。
冷月只是摇了摇头,那张本是温和的脸上,此刻却充满了,一种我们从未见
过的、属于「宗师」的冰冷与理智。
「看着便好。」她的声音,如同这天山之巅万年不化的玄冰,「那啸天魔君
如今看似狂暴,实则早已是外强中干。他体内的魔气,在经历了长时间不间断的
围攻之后,已失了章法,乱了阵脚,他不过是在困兽之斗,强撑着罢了。我敢断
定,他不出一个时辰,必败无疑。」
「此外,」她顿了顿,那双眼眸缓缓地扫过我们二人那充满了年轻热血的脸
庞,「我离恨楼此前已连斩三名护法,若是再将这最后一人也收入囊中,那这
『魔教四大护法皆为离恨楼所杀』的天大功劳,于我离恨楼而言,非但不是好事,
反倒是一场足以招来灭顶之灾的祸端。」
「身在江湖,最怕的就是『第一』。那意味着,我们将会被无数的人追赶,
被无数的势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成为江湖的众矢之的。」
「魔教必会将我离恨楼视作不共戴天的、唯一的死敌,展开最疯狂的、不死
不休的报复;而这江湖之中,所谓的『正道』,也同样会因嫉妒与猜忌,将我离
恨楼视作最大的竞争对手,在暗中百般刁难,甚至落井下石。」
「纵使我们再谨慎,也终有一日会马失前蹄,被他们寻到破绽。你们希望发
生那种事吗?」
「所以,孩子们,」她的声音,带着一种我们尚不能完全理解的、属于成年
人的无奈与智慧,「坐视这场战斗。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看好了,孩子们。看看那些磨洋工的,来自二三流宗门的七品强者吧
……他们既然敢于来到此处,就不可能怕死。可是,他们个个是宗门倾尽全力才
培养出的顶梁柱……他们若是殒命,就几乎等同于宗门的消亡。」
「……看看那些飞蛾扑火的同道吧……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可是这些英雄
的死,只会被最亲密的人所铭记,为他们哭泣。而活着的人,总该放下,终将会
把他们遗忘。那样,他们就真的死了……」
「……烟儿,邵儿……这才是真正的江湖,不只有爱,和所谓『大道』。」
这些话很有道理。
师母说的都是事实。
但我不认可。
「师母,请恕弟子冒犯。您明明不想看他们死,为何不出手?您的领域,弟
子还未亲眼所见,但想必可以轻松胜过那魔头……」
「……弟子愚见……您是想看他们的力量都被消耗,到最后坐收渔翁之利吧?」
我直接将这些突然生出的怀疑讲了出来。
离恨烟瞪了我一眼,但我没停下。
「……是否有朝一日,我和您的女儿,也会成为离恨楼延续下去的『代价』?
也会成为您和鲁楼主的一步棋?」
「……楼主他,压根没有闭关吧?」
我真的怀疑。
她没有正面回答我。
「对,又不对……可是,不论如何……你们必须看着。」
师母的双眼流下泪来。
接下来的话语,却不是令人感动的说辞,而变得愈发冰冷。
「弟子诗剑行听令——一个时辰之后,若是那啸天魔君还未身死,本宗便会
出手,望你在此期间,不再干涉,专心悟道!」
她拿出了属于楼主的威压。
「是……」
这充满了明争暗斗的肮脏江湖,远非我们想象的那般,黑白分明。
它是灰色的。
就如同,一开始的我们,在那黄地主所在的村落之中,善者作恶,恶者行善。
就连我们眼中洁白无瑕的冷月师母……也和她头发上的那一撮黑一样,并非
完美么?
离恨烟也在沉思。
我们只好一同无能为力地旁观这场战斗。
在最惨烈的战场中央,只有四个宗门,还愿意流尽最后一滴血。
只有那些早已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充满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壮决
绝的,真正的英雄,而不是我这种想帮忙,却无能为力的狗熊。
苍云剑派的弟子们,如同最锋利、也最不屈的箭头,组成飘洒如意的苍云剑
阵,义无反顾地冲在了最前方,直指啸天魔君那无比庞大的心口;
风雷阁的弟子们,紧随其后。
他们将自己门派那充满了「迅如风,快如雷」的雷霆拳法,发挥到了极致!
一道道拳风,如同流星雨般,向着那似乎不可战胜的魔神,疯狂地倾泻而去!
而泰山派的弟子们,则沉稳地环绕于四周。
他们将自己那「稳如泰山」、坚不可摧的盾势,组成了一道绵密的盾阵,将
那魔神身上所爆发出的力量余波,给死死地挡在了身前。
那啸天魔君,便如同这狂潮之中最致命的漩涡。他那魁梧的身体,每一次移
动,都带着一股足以让大地都为之颤抖的力量;
他手中那早已被无尽的鲜血与怨念彻底浸透的巨大战斧,每一次挥舞,都卷
起一阵足以将任何六品高手的护体罡气都轻易撕裂的漆黑死亡风暴!
而在战场的边缘,焚天谷……
那位脾气火爆的火长老已经调息完毕,与他身后那数名同样战意滔天的精英
弟子,则如同一群矫健的苍鹰,游走在战场的边缘!
一道道足以焚天煮海的烈焰掌印,与那数道同样是炽热无比的火焰球,如同
一颗颗陨石雨,总能在那魔神身上稍纵即逝的破绽之上,留下一个个充满了焦臭
与毁灭气息的狰狞伤痕!
然而即便如此,战场依旧不是一边倒。
那啸天魔君终究是将七品「化境」修炼至了最圆满的巅峰!
他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手中那饮饱了无数正道豪杰鲜血的巨大战斧,在
瞬间便化作了一道漆黑的死亡龙卷!
「轰——!」
那本是作为锋矢的剑阵,首当其冲!一道道本是清冷凌厉的剑光,在那无可
匹敌的死亡龙卷面前,如同最脆弱的萤火,瞬间便被彻底地吞噬、熄灭!
数名年轻的剑客,甚至连惨叫声都没能发出,便连人带剑,被那狂暴的斧刃
风暴,给彻底地绞成了漫天的血肉碎末!
紧接着,泰山派的盾阵,也被这死亡龙卷生生击碎,数名中坚力量被卷入其
中,瞬间便化作一团血雾!
没了保护,风雷阁的雷霆拳法,也给毫不留情地从中撕裂!
又有数名本是充满了年轻热血的风雷阁弟子,他们的身体便如同一群最脆弱
的瓷娃娃般,被那一斧的能量余波,给轻易地撕裂、斩断!
这些同道……最弱的也达到了五品后期……
看来,我和烟儿在真正的强者面前,确实也只是耗材……炮灰……
那这些同道的死,真的有意义吗……
「风雷诀,起!」
一声如同九天神雷降世的狂暴嘶吼,从那混乱的战场中央,轰然炸响!
风雷阁阁主,七品大圆满- 秦天雷,那张本是充满王者霸气的脸上,此刻,
怒目圆睁!
他看着身旁数名为了守护他,为了守护那所谓的「正道」,而悍不畏死地倒
下的年轻弟子们。
他那双,本是充满了雷霆之威的虎目,红得不似人形!
他将体内的狂野真气,毫无保留地灌注于双拳!
然后,他便像一道狂暴刚猛的紫色闪电般,放弃了所有的防御,向着那魔头,
疯狂地一拳挥出!
「来得好!」
啸天魔君看着那足以将整个天地都彻底撕裂的,恐怖的紫色雷龙。
他居然露出了一个充满戏谑与不屑的病态微笑。
他只是缓缓地抬起了他那只充满了爆炸性力量感的漆黑魔拳。
然后对着那足以将任何低阶高手都轻易撕裂的雷龙,凝聚魔气,接着一拳轰
出!
「轰——!」
紫色雷龙,竟,竟被那看似平平无奇的漆黑魔拳,给毫不留情地从中打断!
而秦天雷那高大的身体,更是如同一只被锋利的刀刃拦腰斩断的麦秆般,向
后倒飞了出去!
「噗——!」
一口鲜血,从他的口中喷出,在空中洒下了一片凄艳的血雾。
「我没事!你们重新结阵,不要停止进攻!」
又是一群飞蛾。
武林正道,正是靠着这般悲壮与决绝的牺牲,来不断地削弱着啸天魔君的实
力!
每一道在他那坚不可摧的魔神之躯上,所留下的狰狞伤痕。
都是用鲜活生命所换来的!
都有意义!
「师母!明明二人都为七品大圆满的实力,为何秦阁主会如此容易就被啸天
魔君击退?」
烟儿忍不住焦急地发问。
「烟儿,你听好。其一,魔气往往比真气更狂暴,因此,同阶高手之中,堕
入魔道者往往强出半分。其二,啸天魔君觉醒的领域,并无规则可言,只能增幅
力量;武林正道皆知如此会让实力再无寸进可能,不会故意觉醒残缺领域,在此
刻反倒成了劣势……」
「其三,秦阁主总是容易大动肝火,只攻不守,在进攻过程之中,极易被找
到破绽。或许,正是这心态,让他的实力再难以寸进,二十多年来,只能卡在七
品圆满……」
是啊,修炼者若想提升境界,力量和心境都必须达到相应的要求。
然而,我看着这地狱,头却越来越痛。
为什么?我好像见过这一切?
在这荒唐的战场之上,绝大部分的所谓「正道同仁」,全都担心被啸天魔君
削弱自己宗门的实力。
他们高举着「替天行道」的旗帜,口中喊着足以让山川都为之变色的激昂口
号,可身体,却很诚实。
那些来自青城、崆峒等二流门派的掌门与长老们,只是远远地缀在战场的边
缘,彼此之间交换着充满了「保存实力」的、心照不宣的眼神。
他们像一群最懦弱的、也最狡猾的鬣狗,远远地退到了战场的边缘。
他们不敢去啃「硬骨头」,只敢将自己那充满了「正义」与「侠义」的爪牙,
对准了那些不成气候的,魔教残兵败将。
我亲眼看到一名潇湘门的「高徒」,用他那「精妙绝伦」的枪法,将一个被
秦天雷阁主的拳罡余波,给震断了双腿的、不成气候的魔教喽啰给「一枪封喉」。
然后,他便像一个拯救了整个天下的盖世英雄般,将自己那沾染了肮脏魔血
的长枪,高高举起,发出一声快意长啸。
那啸声,在真正的战场中央,显得那样的可笑,那样的……不自量力。
不,我不配评价他们的选择。
他们至少还在杀敌,还在略尽绵薄之力。
我却……我却真的认同了师母的说法,选择坐享渔翁。
我为自己,感到羞愧。
时间将近一个时辰。
尸体又多出二十几具。
那焚天谷的火长老,为保护一名泰山派弟子,选择直面斧风,和侯长老一样
重伤倒地。
秦天雷仍在调息。
冷月搂着烟儿,不动声色。
而我,我居然也真的像个有才无德的棋手一样,在这里观看棋子死斗!
这种感觉,和我似是被勾起什么记忆的头颅的胀痛一起传来,让我感觉一阵
反胃。
我再也忍不住了。
去他妈的「渔翁之利」!去他妈的「宗门祸端」!
我诗剑行,或许不懂什么江湖权谋,不懂什么大局为重。
我只知道,我手中的剑,是用来守护的!
死了,就死了!
不管是生是死,我也要贯彻我自己的侠道!
不管这江湖是否黑暗,我都要守护住自己的那寸白!
然而,就在我也即将要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与那些同道们并肩作战的瞬间
——一只无比柔软的素手,死死地拉住了我的胳膊。
是烟儿。
【……剑行……】她的灵魂,在我的脑海之中,发出了一声悲鸣,【……你
若是死了……我……我该怎么办……?】我的身体,猛地一僵。
为何英雄总是败给温柔乡?
大爱,还是小情……
却是如此难以抉择。
「莫急。」
冷月师母那清冷的声音,如一桶冰水,将我那被热血与冲动占据的头脑,浇
得一片冰冷。
「在这战场之上,懂得隐藏气息的,可不止我们几个。」
也正是在这时,那啸天魔君的魔气,果然如冷月所说,再也无法维持那巅峰
的狂暴。
他看着被自己一斧劈得重伤倒地的火长老,那张狰狞的魔脸上,浮现出了一
抹病态的快意。
「老东西!」他痛骂道,「虽然【死局】那几个废物,没能杀掉萧烬那个该
死的伪君子!但今日,能亲手斩下你这老狗的头颅,也算是……无憾了!」
「噗——!」火长老闻言,气急攻心,又是一口鲜血喷涌而出。「你……你
为何……要如此执着于谷主……你们之间,到底有何冤仇?!」
啸天魔君闻言,发出一阵悲凉的狂笑。
「冤仇?」他看着火长老,那双早已被魔气彻底占据的眼眸之中,竟闪过了
一丝不属于魔的、刻骨铭心的痛苦,「……你去自己问他!你问那个为了所谓的
天下大道,便能亲手舍弃自己最重要之人的伪君子!」
「他那所谓的『道』,在我看来,一文不值!只有力量,才是真的!!」
他说着,便不再有丝毫的犹豫,高高地举起了手中那足以开天辟地的巨大战
斧,就要将那失去了所有抵抗能力的火长老,彻底结果!
冷月还是静静地看着。
在她眼里,长老和弟子,或许都只是可以被消耗的蝼蚁,都是有命数的飞蛾
……吗?
不对。
她无需出手!
因为,一道披着黑色长袍、看不清脸的鬼魅身影,此刻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
火长老的身前!
他左手中,一柄通体由黄金所打造、在月光下闪烁着妖异光芒的弯刀,轻描
淡写地,便将那足以开山裂石的巨斧,死死地挡住!
紧接着,一瞬之间,他的右手又从那宽大的黑袍之下,掏出了一柄银光闪闪
的、带着无数狰狞倒刺的流星锤!
那流星锤,如同毒蛇出洞,带着撕裂空气的凄厉尖啸,以一个无比刁钻、无
比致命的角度,向着被这不速之客搅得呆滞一瞬的啸天魔君,反击而去!
啸天魔君被迫收回了那即将要落下的一斧,仓促地,将那巨大的斧面横于胸
前,堪堪挡住了这石破天惊的致命一击!
「铛——!」
一声震耳欲聋的金铁交击之声!
两个同样的强大存在,竟被彼此那狂暴的力量,同时震得向后倒退了数步!
「……【埋骨】……」冷月师母看着那道突然出现的,沾染着黄金精神的神
秘身影,那双总是平静的凤眸,依然风波平平,「……他就是你们在余杭见过迹
象的那个刺客组织——销金楼的楼主,江湖人称『十四刺』的刺客首席……他很
精明。此时出手,恰恰证明那啸天魔君,已经……濒临战败了。我只奇怪,他的
同伴,为何还在隐藏气息?」
也正是在这时,【埋骨】缓缓地转过了头。
他那张隐藏在黑色兜帽之下的、看不清的脸,对着劫后余生的火长老,发出
了一声充满了戏谑与一丝「算你命大」的、沙哑的轻笑。
「……我的好雇主,」他的声音,如同两片干燥的、被黄沙反复打磨过的砂
纸,相互摩擦,「……事成之后,可别忘了给你这位及时赶到的好雇工……多加
点小费啊。」
轻笑声,回荡在这片被鲜血与死亡彻底占据的修罗场上,显得那样的格格不
入,却又……理所当然。
他缓缓地转过身,那张隐藏在黑色兜帽之下的、看不清的脸,对着啸天魔君,
用一种近乎于「例行公事」般的、充满了商人气息的平淡语气,缓缓说道:「
……魔君大人,别来无恙啊。」
「……按我们销金楼的规矩,您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可以活下去的机会。」
「……掏买命钱吧。」
啸天魔君看着眼前这个竟敢在他这「恨天魔相」无上神威面前,还敢如此嚣
张的「蝼蚁」,他那张非人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一丝被彻底羞辱的怒红!
但他终究还是强行压下了心中的怒火。
他也知道自己早已是强弩之末。
「……好!」他从牙缝中,挤出了这个字,「……只要你现在就走!我…
…我魔教宝库之中,所有的金银财宝,任你挑选!」
然而,【埋骨】却只缓缓地摇了摇头。
「……不够。」
「……那再加上我魔教所有的功法秘籍!」
【埋骨】再次摇了摇头。
「……不够。」
「你……你到底想怎么样?!」啸天魔君终于再也无法抑制,发出一声愤怒
的咆哮。
「……不怎么样。」【埋骨】那沙哑的声音,显然是有些「遗憾」,「…
…魔君大人,不是您的价格不够高。而是您的命,现在谁也买不起,您自己也不
行。」
「……我【埋骨】虽是个下贱的刺客,却也还没活够。我可不想因为您这点
小钱,就与整个江湖正道为敌。」
「……而且,」他顿了顿,声音带上了近乎于「催债」般的、理所当然的冰
冷,「……您雇的那支,派去南疆刺杀萧谷主的【死局】小队,如今已是全军覆
没。他们欠我的抽成,还有未来可能提供给我的抽成,我都还没拿到手呢……」
「……所以,魔君大人,您今日还是安心地死在这里吧。」
「……您的这条命,就当是,该给我这个可靠伙伴的……保证金了。」
「你们销金楼的刺客都是臭虫!你是最该死的那一只!」
啸天魔君气得不行,再也无法忍受这般羞辱!他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咆哮,
手中的巨斧,带着足以将整个天地都彻底撕裂的死亡风暴,向着那近在咫尺的、
不知死活的刺客,狠狠地劈了下去!
【埋骨】没有丝毫的惊慌。
他只是,将手中那柄流星锤,随意地,向前一挡。
「轰——!」
那柄坚不可摧的流星锤,竟被那狂暴的斧刃,给当场劈成了漫天的碎片!
而【埋骨】,则借着那股无可匹敌的巨大冲击力,身形如同鬼魅般,向后飘
然退去。
二人就这样,在这片尸横遍野的修罗场上,过了几招。
【埋骨】简直就是个武器大师!
他那件宽大的、看似空无一物的黑色斗篷之下,仿佛藏着一个无穷无尽的武
器库!
他先是掏出了一对分水刺,如毒蛇出洞,轻易地便格开了啸天魔君那足以开
山裂石的狂暴横扫;
他又不知从何处,摸出了一柄沉重的、充满了力量感的八角铜锤,与那魔君
的巨斧,狠狠地,硬撼了一记;
他更是从腰间,抽出了一根九节鞭,那长鞭如同拥有了生命的灵蛇,死死地
缠住了那魔君的脚踝;
耍到最后,他甚至从靴筒里,掏出了一把不过三寸长的蛇牙匕首!
「……魔君大人,」他将那匕首在自己的舌尖,充满了挑逗意味地轻轻舔舐
了一下,「……这上面,可是有我们销金楼,最引以为傲的,触之即死的『情人
泪』哦……」
「您现在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蠢货,就要被自己给毒死了……」
「……不过嘛,」他看着啸天魔君,缓缓地露出了一个,充满了恶作剧意味
的邪笑,「……我只是在开玩笑。」
「您不妨,自己也来舔一口?」
这种视死亡如无物的、不加掩饰的「戏谑」态度,终于将啸天魔君那紧绷到
了极限的最后一丝理智,彻底地点燃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仿佛是在与死亡共舞的、充满了致命魅力的刺客,心中感到
了一阵前所未有的毛骨悚然。
他居然真的,用那把小小的匕首,强行地接下了那魔君的最后,也是最狂暴
的一招!
【埋骨】居然露出了一个邪魅的、「你上当了」的笑容。
因为,那啸天魔君的身后,不知何时,已被「浊尘」神剑,给一剑穿心。
是上官影!
她那娇小的、如同瓷娃娃般的身体,已被鲜血彻底浸透。她那只没握剑的左
臂,更是显然已在此前的战斗中被齐肩斩断!
此刻,她竟拖着这副残破不堪的身体,重返战场!
在啸天魔君被【埋骨】那戏谑与玩味的打法,彻底激怒,将所有的心神都集
中在了他一人身上的,那稍纵即逝的瞬间!
她将自己所有的生命,所有的道,都凝聚在了那最后的、也是最璀璨的一剑
之上!
「……影……要杀你……!」
这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剑」,此刻竟像一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般,发出了
痛苦又感到终于大仇得报的凄厉哭喊!
然而,啸天魔君实在太过强大。
他又发出一声咆哮,一掌将面前的【埋骨】拍飞了出去!
他又用力地,甩了甩自己那如同魔神般的、巨大的身体,竟直接将那贯穿了
他整个心脏的上官影,连人带剑,从自己的身上,狠狠地甩到了地上!
烟儿也和我一样面目惊骇。
她一直以为,自己是这江湖之上唯一一个会用伞的、百年不遇的天才。
却不想,那个被啸天魔君一掌拍飞的【埋骨】,竟在半空之中,同样「唰」
地一声,撑开了一把漆黑的、充满了死亡气息的……
油纸伞。
他以伞消力,轻盈落地,竟是……毫发无伤!
我的……天啊……
【埋骨】看着那从地上挣扎着爬起的、如同断翼蝴蝶般凄美的「天剑」,隐
藏在兜帽之下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不合时宜的玩味笑容。
他颇为绅士地,对着上官影,微微躬身行了一礼。
「……上官女侠,」他那沙哑的声音,充满了戏谑,「……看您这副模样,
想必是需要一些小小的帮助吧?」
「……只要您肯花点小钱,给我拿来买几件新兵器,我便将您安然无恙地从
魔君的斧头下救出去。」
「……当然,」他顿了顿,那沙哑的声音,带上了一丝近乎于「调戏」的轻
佻,「……若是您同意让我花大钱,买下您这春宵一刻……」
「……在下倒也还从未尝过,您这般用驻颜术保养得当的、活了上百年的
『老萝莉』,究竟是何等的滋味呢……」
上官影死死地咬住嘴唇,她那张可爱的脸庞,因为极致的愤怒与屈辱,而涨
得一片通红。
但她,终究还是从牙缝中,挤出了一个字。
「……好。」
她当然只是想「花小钱」。
【埋骨】发出一声满足的轻笑。
他再次撑开那柄黑色的油纸伞,身形如同鬼魅般,在那狂暴的斧刃风暴之中,
再次将上官影安然无恙地救了回来。
代价是,那柄不知是何材质的油纸伞,被那狂暴的魔气,给当场绞成了漫天
的碎片。
【埋骨】收手了。
「……唉,」他看着自己那光秃秃的伞柄,发出一声肉疼的叹息,「……我
还有八十种兵器,但是可不想再损坏了。如果那样……我这一趟,可就真的回不
了本了。」
「骗你们的……里面可装不了八十种,只有……好多种。」
我已经开始逐渐习惯他的黑色幽默了。
然而,上官影那拼上了性命的最后一剑,终究还是起到了作用。
啸天魔君那本是如同实质般的护体魔气,此刻,正如同一个被戳破了的气球
般,不受控制地向外疯狂地泄露着!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那本是如同磐石般的防御,此刻已然是破绽百出!
我的全力一击,已经足以将他破防!
我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战意,就要冲上前去!而身旁的烟儿,也同样意识到
了转瞬即逝的战机,准备与我一同进击,或是赴死!
然而,我们还是动不了。
因为,师母不放人。
因为,那泰山派的另一位娄长老,与那刚刚才从调息之中强行站起的秦天雷,
早已先我们一步,发动了最后的冲锋!
「老娄!跟老子一起上!」秦天雷吐出一口淤血,将体内所有的雷霆真气,
都凝聚于右拳之上!
「为了盟主!」娄长老同样发出一声怒吼,将他那面刻有泰山图腾的巨大盾
牌,如同最坚固的、最不屈的磐石,狠狠地向着那啸天魔君,撞了过去!
啸天魔君一斧将那本已是身受重伤,也不想和他同归于尽的秦天雷,再次击
退!
又一斧,则狠狠地砍在了娄长老的盾牌之上,将他整个人,都如同钉子般,
死死地压在了那冰冷坚硬的玄冰地面之下!
冷月已经抬起手来。
她这是终于要出手了?
「以血研墨,落笔成书。」
一声清冷不带丝毫感情的、雌雄莫辨的音色,却突然在这战场之上,缓缓响
起。
冷月放下手,轻声笑了起来——那【埋骨】的同伴,终于是开口了。
只见另一个黑袍刺客,不知何时,已然出现在了战场的中央。
那人瘦削无比,全身都隐藏在极为贴身的黑纱长袍之下,一头及腰的黑色长
发,在风雪之中狂舞。
胸部平平无奇,看不出是男是女。
手中,正握着一支,由不知名的、散发着淡淡幽光的纯白色神兽骸骨所打造
的骨笔。
此人居然以那冰冷的、沾满了鲜血的玄冰为纸,以那不知是谁的、温热的鲜
血为墨,在战场中央,飞速地书写着什么。
当那符文最后一笔落下的瞬间,将一口充满了自己生命本源的精血,狠狠地
吐了上去!
「莫动。」
啸天魔君的巨大魔躯,猛地一僵!他的行动,竟真的变得迟缓了!
「弃防。」
又一口精血。
他正在疯狂外泄的护体魔气,竟真的如同被阳光融化的冰雪般,进一步迅速
地减弱了!
「你……你到底是谁?!」
魔君惊骇地问道。
那人一句话不说。
【埋骨】则像一个最懂得把握时机的商人般,隆重地环绕全场鞠了一躬,向
在场所有的武林同道,也是他所有的潜在客户们,介绍着他这位,全新的神秘同
伴。
「……诸位,容我介绍一下,想必你们也是头次见,」他那沙哑的声音,充
满了不加掩饰的得意,「……这位便是我销金楼,新晋的第三刺客——【天谴】。」
「……欢迎大家,多多找他下订单!他一个人,就可以轻松胜过那三个,已
经死在了南疆的【死局】哦~」
「当然,他也和我一样,不会收那马上就要死的,就连我们刺客都唾弃的魔
头的钱……」
他嘲讽完这最后一句,便准备冲上前去,亲手结果了这已是囊中之物的啸天
魔君!
不行,不能让这刺客抢先。
那颗英雄心让我猛地拔剑,临渊出鞘。
「魔头,受死!」
一声属于年轻王者的嘹亮嘶吼,轰然炸响!
喊出这一声的,却不是我。
我已经被冷月一把按在地上啃雪了。
一道身着白袍的身影,比我更快,也比他更快!
他一手持足以洞穿一切的霸王枪,一手持足以斩断一切的君子剑,如同一道
金色闪电,转瞬便出现在了啸天魔君面前!
「滚!」
啸天魔君咆哮一声,就要提斧格挡。
「澄儿!不可!」那被死死压在地上的娄长老,发出一声恨铁不成钢的怒吼。
但他终究还是用自己的盾牌,死死地钳住了那魔君即将要回防的巨斧!
啸天魔君只好将所能调集的魔气全部用来防御,但已经迟了!
在那魔头充满了杀意……与憾意的眼眸注视下,枪出如龙,剑出如虹!
七品前期,「武林少盟主」——宇文澄,一枪扎进了那被上官影一剑穿心的、
同一个伤口!
另一剑……
「噗嗤——!」
一颗带着无尽狂妄与不甘的、狰狞的头颅,冲天而起!
我怔怔地看着那道在尸山血海之中傲然而立的、不比我年长多少的身影。
我的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我居然还曾以为,他不过是个只会仗着自己父亲的威名,作威作福的废物纨
绔!
没想到,他的实力,竟然已达七品化境前期!
我没有资格鄙夷他。
他比我……强得太多。
「这孩子叫宇文澄。你敢与他争这啸天魔君的人头吗?」
冷月师母那平静的声音,缓缓地在我耳边响起。
她看着那道年轻气盛、不可一世的最终「英雄」,闪过了一丝极其复杂、我
读不懂的情绪。
那里面,有赞许,有欣赏,也有一丝……隐藏得极深的担忧。
我收回临渊。
我扭过头去。
我不愿意承认,那冷漠得不像是烟儿母亲的宗师,是对的。
可她,确实是对的。
这一天,我学到很多。
太多了。
天山之上的第五战,就这样胜了。
可是,和我半文钱关系也没有。
2025年8月25日2首发:第一会所
字数:12295
写在前面:笔者自觉在写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必须要有优秀的武戏和文戏。
这一章里,笔者自认做到了这两点。
感兴趣的诸君很快就会看到数个全新的【领域】。
祝读得愉快。
第十六章:啸天魔君
诗剑行躺在雪地上。
我与离恨烟在冰冷的雪地中温暖地相拥,休息了一会,享受爱意的余韵。
凛冽的寒风在我们身周呼啸,却丝毫无法侵入那由我们二人体温与爱意共同
构筑的、小小的温暖结界。
她的呼吸平稳而均匀,轻柔地扑洒在我的颈间,带着一丝独属于她的、兰花
般的幽香,和一丝我们二人刚刚才在欢爱之中所留下的、充满生命力的甜腻气息。
离恨烟轻轻抚摸着我的脸,那冰凉的、却又无比柔软的指尖,在我那因为连
场激战而显得有些胡子拉碴的下巴上,缓缓地游走、爱怜。而我则将我的手覆在
她被我开发得无比敏感、手感绝佳的雪峰之上,不轻不重地缓缓揉捏。
这是我们应得的安宁。
然而,这份宁静,却再一次被一道温婉身影给毫不留情地打断了。
冷月师母,不知何时,已如鬼魅般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这已经是不知多少次,她打断我们做爱了。
我心里甚至生出一种不敢说出的奇怪想法。
她……她是不是有偷窥别人欢爱的癖好啊?
不行不行!李邵!你这个畜生!
她可是你师母!
是你在这世上,除了烟儿之外,最亲的家人!
你怎么能用这般龌龊的念头去想她?!
我心中那刚刚才冒出头的、大不敬的念头,瞬间便被一股更加强烈的、足以
将我灵魂都彻底淹没的无边愧疚,给彻底地掐灭了。
「孩儿们,穿好衣服吧,」师母看着我们这副衣衫不整、紧紧纠缠在一起的
尴尬模样,她脸上却没有丝毫的波澜,仿佛早已司空见惯,「为师要带你们,去
那围攻最后一位护法——啸天魔君的战场……」
我和烟儿看着自己那并未完全恢复的身体,都有些迟疑。
我们早已从媚儿口中得知,那啸天魔君乃是七品大圆满高手,而且心智成熟,
远非那头脑简单的血手阎罗和那像雌小鬼一样的娇奴可比。
我俩能有什么用?
难道师母竟忍心,让我们这两个刚刚才在她面前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小
英雄」,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去当炮灰吗?
冷月只是轻轻拉起我们。
她那双保养得宜的手,看似轻柔,却又带着一股我们根本无法抗拒的力量。
我们只好跟着她前行。
没过一会,我们便来到那尸山血海面前。
那是一幅我此生都再也无法忘怀的,充满了无尽的悲壮、惨烈与一丝……荒
唐的景象。
我们脚下是被无尽的鲜血与残肢断臂彻底染成一片触目惊心的妖异暗红色的
万载玄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充满了血腥、焦臭与浓郁魔气的死亡
味道。
数以十计来自各大门派的、本该是意气风发的正道豪杰,以及数百具恶鬼的
残尸,此刻却如同一堆堆最卑贱的破烂垃圾般,横七竖八、不分敌我地倒在那冰
冷的、肮脏的血泊之中。?也正是在我们抵达的这一刻,正好目睹了那足以让任
何人都为之胆寒的一幕。
在前日的会议之中,与秦阁主险些动手的,那来自?泰山派的侯长老,他手
中的拂尘已被鲜血浸透,此刻正须发皆张,拼尽全力地抵挡着那如同山岳般砸下
的巨斧。
然而,只听「咔嚓」两声脆响,他那两条仙风道骨的手臂,竟被势不可挡的
巨斧,连同护体的法宝,一同硬生生地斩断!?」老侯!」?秦天雷的身形立刻
化作一道紫色的雷光,在那位长老即将被后续的斧刃彻底劈成两半的瞬间,将他
那血流如注的残躯,险之又险地从那死亡的阴影之下抢救了出来。?放眼望去,
整个战场之上,「天剑」上官影此刻竟不见了踪影;
而焚天谷那位脾气火爆的火长老,也同样是脸色煞白地盘坐在一旁,显然是
真气耗尽,正在紧急地调息。?整个正道联军,竟已被逼入了即将要彻底崩溃的
绝境!?而造成这一切的,便是那个屹立于尸山血海中央的、如同上古魔神般的
恐怖巨人。?那是一尊高达数十丈、青面獠牙、肌肉虬结的怪物。他那如同熔岩
般的皮肤之上,布满了充满了怨念的黑色魔纹;他的口中,不断地喷吐着足以将
空气都彻底点燃的硫磺气息。?我与烟儿看着眼前这尊已超越我们所有想象的
「法天象地」,我们那颗刚刚才在连番大战之中被淬炼得坚如磐石的道心,不受
控制地剧烈颤抖了起来。?我们竟被吓到了。
我们就呆呆地看着,一些尚有一战之力的武林同道已杀红了眼。
他们像一群野兽,发出一声声嘶吼,向着那被他们死死地围困在战场中央的
庞大目标,疯狂地冲了上去!
然而,所有攻击,在落到他那被如同实质般的黑色护体魔气,所彻底包裹的
身体之上的瞬间,便如同一颗颗投入无边无际、汹涌大海之中的微不足道石子般,
被他那诡异如同无底洞般的魔气吞噬!
而那些,本该是这场「正邪大战」之中的中坚力量——那些来自其他二三流
门派、达到了七品「化境」的宗主们,此刻却都跑去清理战场上的魔教杂兵与都
统。
只有少数几名强者,偶尔出手与那魔头过招,但只是几个回合之后便拉开,
生怕自己受伤。?也正是在这时,师母冷月那清冷的、却又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
平静的声音,在我们耳边缓缓响起。?」不必惊慌。」?」……那是『恨天魔相』,
只不过是个为了追求力量,而亲手毁了自己未来的『残缺领域』罢了。」
这句话让我们冷静下来,又顿时变成了义愤填膺。
「剑行……这该死的魔头……!」
离恨烟的声音嘶哑而愤怒,她那原本清冷的气质,此刻却被一种凌厉的杀意
所取代。
我们本想上前助阵,用我二人那心意相通的合击剑法,去助那些强弩之末的
同道一臂之力,却被冷月师母那只冰凉的手,死死地按住了。
她早已施展秘法,把我们的身形气息彻底隐藏。
「师母?」烟儿那双清澈的眼眸之中充满了不解与一丝焦急。
冷月只是摇了摇头,那张本是温和的脸上,此刻却充满了,一种我们从未见
过的、属于「宗师」的冰冷与理智。
「看着便好。」她的声音,如同这天山之巅万年不化的玄冰,「那啸天魔君
如今看似狂暴,实则早已是外强中干。他体内的魔气,在经历了长时间不间断的
围攻之后,已失了章法,乱了阵脚,他不过是在困兽之斗,强撑着罢了。我敢断
定,他不出一个时辰,必败无疑。」
「此外,」她顿了顿,那双眼眸缓缓地扫过我们二人那充满了年轻热血的脸
庞,「我离恨楼此前已连斩三名护法,若是再将这最后一人也收入囊中,那这
『魔教四大护法皆为离恨楼所杀』的天大功劳,于我离恨楼而言,非但不是好事,
反倒是一场足以招来灭顶之灾的祸端。」
「身在江湖,最怕的就是『第一』。那意味着,我们将会被无数的人追赶,
被无数的势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成为江湖的众矢之的。」
「魔教必会将我离恨楼视作不共戴天的、唯一的死敌,展开最疯狂的、不死
不休的报复;而这江湖之中,所谓的『正道』,也同样会因嫉妒与猜忌,将我离
恨楼视作最大的竞争对手,在暗中百般刁难,甚至落井下石。」
「纵使我们再谨慎,也终有一日会马失前蹄,被他们寻到破绽。你们希望发
生那种事吗?」
「所以,孩子们,」她的声音,带着一种我们尚不能完全理解的、属于成年
人的无奈与智慧,「坐视这场战斗。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看好了,孩子们。看看那些磨洋工的,来自二三流宗门的七品强者吧
……他们既然敢于来到此处,就不可能怕死。可是,他们个个是宗门倾尽全力才
培养出的顶梁柱……他们若是殒命,就几乎等同于宗门的消亡。」
「……看看那些飞蛾扑火的同道吧……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可是这些英雄
的死,只会被最亲密的人所铭记,为他们哭泣。而活着的人,总该放下,终将会
把他们遗忘。那样,他们就真的死了……」
「……烟儿,邵儿……这才是真正的江湖,不只有爱,和所谓『大道』。」
这些话很有道理。
师母说的都是事实。
但我不认可。
「师母,请恕弟子冒犯。您明明不想看他们死,为何不出手?您的领域,弟
子还未亲眼所见,但想必可以轻松胜过那魔头……」
「……弟子愚见……您是想看他们的力量都被消耗,到最后坐收渔翁之利吧?」
我直接将这些突然生出的怀疑讲了出来。
离恨烟瞪了我一眼,但我没停下。
「……是否有朝一日,我和您的女儿,也会成为离恨楼延续下去的『代价』?
也会成为您和鲁楼主的一步棋?」
「……楼主他,压根没有闭关吧?」
我真的怀疑。
她没有正面回答我。
「对,又不对……可是,不论如何……你们必须看着。」
师母的双眼流下泪来。
接下来的话语,却不是令人感动的说辞,而变得愈发冰冷。
「弟子诗剑行听令——一个时辰之后,若是那啸天魔君还未身死,本宗便会
出手,望你在此期间,不再干涉,专心悟道!」
她拿出了属于楼主的威压。
「是……」
这充满了明争暗斗的肮脏江湖,远非我们想象的那般,黑白分明。
它是灰色的。
就如同,一开始的我们,在那黄地主所在的村落之中,善者作恶,恶者行善。
就连我们眼中洁白无瑕的冷月师母……也和她头发上的那一撮黑一样,并非
完美么?
离恨烟也在沉思。
我们只好一同无能为力地旁观这场战斗。
在最惨烈的战场中央,只有四个宗门,还愿意流尽最后一滴血。
只有那些早已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充满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壮决
绝的,真正的英雄,而不是我这种想帮忙,却无能为力的狗熊。
苍云剑派的弟子们,如同最锋利、也最不屈的箭头,组成飘洒如意的苍云剑
阵,义无反顾地冲在了最前方,直指啸天魔君那无比庞大的心口;
风雷阁的弟子们,紧随其后。
他们将自己门派那充满了「迅如风,快如雷」的雷霆拳法,发挥到了极致!
一道道拳风,如同流星雨般,向着那似乎不可战胜的魔神,疯狂地倾泻而去!
而泰山派的弟子们,则沉稳地环绕于四周。
他们将自己那「稳如泰山」、坚不可摧的盾势,组成了一道绵密的盾阵,将
那魔神身上所爆发出的力量余波,给死死地挡在了身前。
那啸天魔君,便如同这狂潮之中最致命的漩涡。他那魁梧的身体,每一次移
动,都带着一股足以让大地都为之颤抖的力量;
他手中那早已被无尽的鲜血与怨念彻底浸透的巨大战斧,每一次挥舞,都卷
起一阵足以将任何六品高手的护体罡气都轻易撕裂的漆黑死亡风暴!
而在战场的边缘,焚天谷……
那位脾气火爆的火长老已经调息完毕,与他身后那数名同样战意滔天的精英
弟子,则如同一群矫健的苍鹰,游走在战场的边缘!
一道道足以焚天煮海的烈焰掌印,与那数道同样是炽热无比的火焰球,如同
一颗颗陨石雨,总能在那魔神身上稍纵即逝的破绽之上,留下一个个充满了焦臭
与毁灭气息的狰狞伤痕!
然而即便如此,战场依旧不是一边倒。
那啸天魔君终究是将七品「化境」修炼至了最圆满的巅峰!
他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手中那饮饱了无数正道豪杰鲜血的巨大战斧,在
瞬间便化作了一道漆黑的死亡龙卷!
「轰——!」
那本是作为锋矢的剑阵,首当其冲!一道道本是清冷凌厉的剑光,在那无可
匹敌的死亡龙卷面前,如同最脆弱的萤火,瞬间便被彻底地吞噬、熄灭!
数名年轻的剑客,甚至连惨叫声都没能发出,便连人带剑,被那狂暴的斧刃
风暴,给彻底地绞成了漫天的血肉碎末!
紧接着,泰山派的盾阵,也被这死亡龙卷生生击碎,数名中坚力量被卷入其
中,瞬间便化作一团血雾!
没了保护,风雷阁的雷霆拳法,也给毫不留情地从中撕裂!
又有数名本是充满了年轻热血的风雷阁弟子,他们的身体便如同一群最脆弱
的瓷娃娃般,被那一斧的能量余波,给轻易地撕裂、斩断!
这些同道……最弱的也达到了五品后期……
看来,我和烟儿在真正的强者面前,确实也只是耗材……炮灰……
那这些同道的死,真的有意义吗……
「风雷诀,起!」
一声如同九天神雷降世的狂暴嘶吼,从那混乱的战场中央,轰然炸响!
风雷阁阁主,七品大圆满- 秦天雷,那张本是充满王者霸气的脸上,此刻,
怒目圆睁!
他看着身旁数名为了守护他,为了守护那所谓的「正道」,而悍不畏死地倒
下的年轻弟子们。
他那双,本是充满了雷霆之威的虎目,红得不似人形!
他将体内的狂野真气,毫无保留地灌注于双拳!
然后,他便像一道狂暴刚猛的紫色闪电般,放弃了所有的防御,向着那魔头,
疯狂地一拳挥出!
「来得好!」
啸天魔君看着那足以将整个天地都彻底撕裂的,恐怖的紫色雷龙。
他居然露出了一个充满戏谑与不屑的病态微笑。
他只是缓缓地抬起了他那只充满了爆炸性力量感的漆黑魔拳。
然后对着那足以将任何低阶高手都轻易撕裂的雷龙,凝聚魔气,接着一拳轰
出!
「轰——!」
紫色雷龙,竟,竟被那看似平平无奇的漆黑魔拳,给毫不留情地从中打断!
而秦天雷那高大的身体,更是如同一只被锋利的刀刃拦腰斩断的麦秆般,向
后倒飞了出去!
「噗——!」
一口鲜血,从他的口中喷出,在空中洒下了一片凄艳的血雾。
「我没事!你们重新结阵,不要停止进攻!」
又是一群飞蛾。
武林正道,正是靠着这般悲壮与决绝的牺牲,来不断地削弱着啸天魔君的实
力!
每一道在他那坚不可摧的魔神之躯上,所留下的狰狞伤痕。
都是用鲜活生命所换来的!
都有意义!
「师母!明明二人都为七品大圆满的实力,为何秦阁主会如此容易就被啸天
魔君击退?」
烟儿忍不住焦急地发问。
「烟儿,你听好。其一,魔气往往比真气更狂暴,因此,同阶高手之中,堕
入魔道者往往强出半分。其二,啸天魔君觉醒的领域,并无规则可言,只能增幅
力量;武林正道皆知如此会让实力再无寸进可能,不会故意觉醒残缺领域,在此
刻反倒成了劣势……」
「其三,秦阁主总是容易大动肝火,只攻不守,在进攻过程之中,极易被找
到破绽。或许,正是这心态,让他的实力再难以寸进,二十多年来,只能卡在七
品圆满……」
是啊,修炼者若想提升境界,力量和心境都必须达到相应的要求。
然而,我看着这地狱,头却越来越痛。
为什么?我好像见过这一切?
在这荒唐的战场之上,绝大部分的所谓「正道同仁」,全都担心被啸天魔君
削弱自己宗门的实力。
他们高举着「替天行道」的旗帜,口中喊着足以让山川都为之变色的激昂口
号,可身体,却很诚实。
那些来自青城、崆峒等二流门派的掌门与长老们,只是远远地缀在战场的边
缘,彼此之间交换着充满了「保存实力」的、心照不宣的眼神。
他们像一群最懦弱的、也最狡猾的鬣狗,远远地退到了战场的边缘。
他们不敢去啃「硬骨头」,只敢将自己那充满了「正义」与「侠义」的爪牙,
对准了那些不成气候的,魔教残兵败将。
我亲眼看到一名潇湘门的「高徒」,用他那「精妙绝伦」的枪法,将一个被
秦天雷阁主的拳罡余波,给震断了双腿的、不成气候的魔教喽啰给「一枪封喉」。
然后,他便像一个拯救了整个天下的盖世英雄般,将自己那沾染了肮脏魔血
的长枪,高高举起,发出一声快意长啸。
那啸声,在真正的战场中央,显得那样的可笑,那样的……不自量力。
不,我不配评价他们的选择。
他们至少还在杀敌,还在略尽绵薄之力。
我却……我却真的认同了师母的说法,选择坐享渔翁。
我为自己,感到羞愧。
时间将近一个时辰。
尸体又多出二十几具。
那焚天谷的火长老,为保护一名泰山派弟子,选择直面斧风,和侯长老一样
重伤倒地。
秦天雷仍在调息。
冷月搂着烟儿,不动声色。
而我,我居然也真的像个有才无德的棋手一样,在这里观看棋子死斗!
这种感觉,和我似是被勾起什么记忆的头颅的胀痛一起传来,让我感觉一阵
反胃。
我再也忍不住了。
去他妈的「渔翁之利」!去他妈的「宗门祸端」!
我诗剑行,或许不懂什么江湖权谋,不懂什么大局为重。
我只知道,我手中的剑,是用来守护的!
死了,就死了!
不管是生是死,我也要贯彻我自己的侠道!
不管这江湖是否黑暗,我都要守护住自己的那寸白!
然而,就在我也即将要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与那些同道们并肩作战的瞬间
——一只无比柔软的素手,死死地拉住了我的胳膊。
是烟儿。
【……剑行……】她的灵魂,在我的脑海之中,发出了一声悲鸣,【……你
若是死了……我……我该怎么办……?】我的身体,猛地一僵。
为何英雄总是败给温柔乡?
大爱,还是小情……
却是如此难以抉择。
「莫急。」
冷月师母那清冷的声音,如一桶冰水,将我那被热血与冲动占据的头脑,浇
得一片冰冷。
「在这战场之上,懂得隐藏气息的,可不止我们几个。」
也正是在这时,那啸天魔君的魔气,果然如冷月所说,再也无法维持那巅峰
的狂暴。
他看着被自己一斧劈得重伤倒地的火长老,那张狰狞的魔脸上,浮现出了一
抹病态的快意。
「老东西!」他痛骂道,「虽然【死局】那几个废物,没能杀掉萧烬那个该
死的伪君子!但今日,能亲手斩下你这老狗的头颅,也算是……无憾了!」
「噗——!」火长老闻言,气急攻心,又是一口鲜血喷涌而出。「你……你
为何……要如此执着于谷主……你们之间,到底有何冤仇?!」
啸天魔君闻言,发出一阵悲凉的狂笑。
「冤仇?」他看着火长老,那双早已被魔气彻底占据的眼眸之中,竟闪过了
一丝不属于魔的、刻骨铭心的痛苦,「……你去自己问他!你问那个为了所谓的
天下大道,便能亲手舍弃自己最重要之人的伪君子!」
「他那所谓的『道』,在我看来,一文不值!只有力量,才是真的!!」
他说着,便不再有丝毫的犹豫,高高地举起了手中那足以开天辟地的巨大战
斧,就要将那失去了所有抵抗能力的火长老,彻底结果!
冷月还是静静地看着。
在她眼里,长老和弟子,或许都只是可以被消耗的蝼蚁,都是有命数的飞蛾
……吗?
不对。
她无需出手!
因为,一道披着黑色长袍、看不清脸的鬼魅身影,此刻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
火长老的身前!
他左手中,一柄通体由黄金所打造、在月光下闪烁着妖异光芒的弯刀,轻描
淡写地,便将那足以开山裂石的巨斧,死死地挡住!
紧接着,一瞬之间,他的右手又从那宽大的黑袍之下,掏出了一柄银光闪闪
的、带着无数狰狞倒刺的流星锤!
那流星锤,如同毒蛇出洞,带着撕裂空气的凄厉尖啸,以一个无比刁钻、无
比致命的角度,向着被这不速之客搅得呆滞一瞬的啸天魔君,反击而去!
啸天魔君被迫收回了那即将要落下的一斧,仓促地,将那巨大的斧面横于胸
前,堪堪挡住了这石破天惊的致命一击!
「铛——!」
一声震耳欲聋的金铁交击之声!
两个同样的强大存在,竟被彼此那狂暴的力量,同时震得向后倒退了数步!
「……【埋骨】……」冷月师母看着那道突然出现的,沾染着黄金精神的神
秘身影,那双总是平静的凤眸,依然风波平平,「……他就是你们在余杭见过迹
象的那个刺客组织——销金楼的楼主,江湖人称『十四刺』的刺客首席……他很
精明。此时出手,恰恰证明那啸天魔君,已经……濒临战败了。我只奇怪,他的
同伴,为何还在隐藏气息?」
也正是在这时,【埋骨】缓缓地转过了头。
他那张隐藏在黑色兜帽之下的、看不清的脸,对着劫后余生的火长老,发出
了一声充满了戏谑与一丝「算你命大」的、沙哑的轻笑。
「……我的好雇主,」他的声音,如同两片干燥的、被黄沙反复打磨过的砂
纸,相互摩擦,「……事成之后,可别忘了给你这位及时赶到的好雇工……多加
点小费啊。」
轻笑声,回荡在这片被鲜血与死亡彻底占据的修罗场上,显得那样的格格不
入,却又……理所当然。
他缓缓地转过身,那张隐藏在黑色兜帽之下的、看不清的脸,对着啸天魔君,
用一种近乎于「例行公事」般的、充满了商人气息的平淡语气,缓缓说道:「
……魔君大人,别来无恙啊。」
「……按我们销金楼的规矩,您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可以活下去的机会。」
「……掏买命钱吧。」
啸天魔君看着眼前这个竟敢在他这「恨天魔相」无上神威面前,还敢如此嚣
张的「蝼蚁」,他那张非人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一丝被彻底羞辱的怒红!
但他终究还是强行压下了心中的怒火。
他也知道自己早已是强弩之末。
「……好!」他从牙缝中,挤出了这个字,「……只要你现在就走!我…
…我魔教宝库之中,所有的金银财宝,任你挑选!」
然而,【埋骨】却只缓缓地摇了摇头。
「……不够。」
「……那再加上我魔教所有的功法秘籍!」
【埋骨】再次摇了摇头。
「……不够。」
「你……你到底想怎么样?!」啸天魔君终于再也无法抑制,发出一声愤怒
的咆哮。
「……不怎么样。」【埋骨】那沙哑的声音,显然是有些「遗憾」,「…
…魔君大人,不是您的价格不够高。而是您的命,现在谁也买不起,您自己也不
行。」
「……我【埋骨】虽是个下贱的刺客,却也还没活够。我可不想因为您这点
小钱,就与整个江湖正道为敌。」
「……而且,」他顿了顿,声音带上了近乎于「催债」般的、理所当然的冰
冷,「……您雇的那支,派去南疆刺杀萧谷主的【死局】小队,如今已是全军覆
没。他们欠我的抽成,还有未来可能提供给我的抽成,我都还没拿到手呢……」
「……所以,魔君大人,您今日还是安心地死在这里吧。」
「……您的这条命,就当是,该给我这个可靠伙伴的……保证金了。」
「你们销金楼的刺客都是臭虫!你是最该死的那一只!」
啸天魔君气得不行,再也无法忍受这般羞辱!他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咆哮,
手中的巨斧,带着足以将整个天地都彻底撕裂的死亡风暴,向着那近在咫尺的、
不知死活的刺客,狠狠地劈了下去!
【埋骨】没有丝毫的惊慌。
他只是,将手中那柄流星锤,随意地,向前一挡。
「轰——!」
那柄坚不可摧的流星锤,竟被那狂暴的斧刃,给当场劈成了漫天的碎片!
而【埋骨】,则借着那股无可匹敌的巨大冲击力,身形如同鬼魅般,向后飘
然退去。
二人就这样,在这片尸横遍野的修罗场上,过了几招。
【埋骨】简直就是个武器大师!
他那件宽大的、看似空无一物的黑色斗篷之下,仿佛藏着一个无穷无尽的武
器库!
他先是掏出了一对分水刺,如毒蛇出洞,轻易地便格开了啸天魔君那足以开
山裂石的狂暴横扫;
他又不知从何处,摸出了一柄沉重的、充满了力量感的八角铜锤,与那魔君
的巨斧,狠狠地,硬撼了一记;
他更是从腰间,抽出了一根九节鞭,那长鞭如同拥有了生命的灵蛇,死死地
缠住了那魔君的脚踝;
耍到最后,他甚至从靴筒里,掏出了一把不过三寸长的蛇牙匕首!
「……魔君大人,」他将那匕首在自己的舌尖,充满了挑逗意味地轻轻舔舐
了一下,「……这上面,可是有我们销金楼,最引以为傲的,触之即死的『情人
泪』哦……」
「您现在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蠢货,就要被自己给毒死了……」
「……不过嘛,」他看着啸天魔君,缓缓地露出了一个,充满了恶作剧意味
的邪笑,「……我只是在开玩笑。」
「您不妨,自己也来舔一口?」
这种视死亡如无物的、不加掩饰的「戏谑」态度,终于将啸天魔君那紧绷到
了极限的最后一丝理智,彻底地点燃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仿佛是在与死亡共舞的、充满了致命魅力的刺客,心中感到
了一阵前所未有的毛骨悚然。
他居然真的,用那把小小的匕首,强行地接下了那魔君的最后,也是最狂暴
的一招!
【埋骨】居然露出了一个邪魅的、「你上当了」的笑容。
因为,那啸天魔君的身后,不知何时,已被「浊尘」神剑,给一剑穿心。
是上官影!
她那娇小的、如同瓷娃娃般的身体,已被鲜血彻底浸透。她那只没握剑的左
臂,更是显然已在此前的战斗中被齐肩斩断!
此刻,她竟拖着这副残破不堪的身体,重返战场!
在啸天魔君被【埋骨】那戏谑与玩味的打法,彻底激怒,将所有的心神都集
中在了他一人身上的,那稍纵即逝的瞬间!
她将自己所有的生命,所有的道,都凝聚在了那最后的、也是最璀璨的一剑
之上!
「……影……要杀你……!」
这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剑」,此刻竟像一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般,发出了
痛苦又感到终于大仇得报的凄厉哭喊!
然而,啸天魔君实在太过强大。
他又发出一声咆哮,一掌将面前的【埋骨】拍飞了出去!
他又用力地,甩了甩自己那如同魔神般的、巨大的身体,竟直接将那贯穿了
他整个心脏的上官影,连人带剑,从自己的身上,狠狠地甩到了地上!
烟儿也和我一样面目惊骇。
她一直以为,自己是这江湖之上唯一一个会用伞的、百年不遇的天才。
却不想,那个被啸天魔君一掌拍飞的【埋骨】,竟在半空之中,同样「唰」
地一声,撑开了一把漆黑的、充满了死亡气息的……
油纸伞。
他以伞消力,轻盈落地,竟是……毫发无伤!
我的……天啊……
【埋骨】看着那从地上挣扎着爬起的、如同断翼蝴蝶般凄美的「天剑」,隐
藏在兜帽之下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不合时宜的玩味笑容。
他颇为绅士地,对着上官影,微微躬身行了一礼。
「……上官女侠,」他那沙哑的声音,充满了戏谑,「……看您这副模样,
想必是需要一些小小的帮助吧?」
「……只要您肯花点小钱,给我拿来买几件新兵器,我便将您安然无恙地从
魔君的斧头下救出去。」
「……当然,」他顿了顿,那沙哑的声音,带上了一丝近乎于「调戏」的轻
佻,「……若是您同意让我花大钱,买下您这春宵一刻……」
「……在下倒也还从未尝过,您这般用驻颜术保养得当的、活了上百年的
『老萝莉』,究竟是何等的滋味呢……」
上官影死死地咬住嘴唇,她那张可爱的脸庞,因为极致的愤怒与屈辱,而涨
得一片通红。
但她,终究还是从牙缝中,挤出了一个字。
「……好。」
她当然只是想「花小钱」。
【埋骨】发出一声满足的轻笑。
他再次撑开那柄黑色的油纸伞,身形如同鬼魅般,在那狂暴的斧刃风暴之中,
再次将上官影安然无恙地救了回来。
代价是,那柄不知是何材质的油纸伞,被那狂暴的魔气,给当场绞成了漫天
的碎片。
【埋骨】收手了。
「……唉,」他看着自己那光秃秃的伞柄,发出一声肉疼的叹息,「……我
还有八十种兵器,但是可不想再损坏了。如果那样……我这一趟,可就真的回不
了本了。」
「骗你们的……里面可装不了八十种,只有……好多种。」
我已经开始逐渐习惯他的黑色幽默了。
然而,上官影那拼上了性命的最后一剑,终究还是起到了作用。
啸天魔君那本是如同实质般的护体魔气,此刻,正如同一个被戳破了的气球
般,不受控制地向外疯狂地泄露着!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那本是如同磐石般的防御,此刻已然是破绽百出!
我的全力一击,已经足以将他破防!
我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战意,就要冲上前去!而身旁的烟儿,也同样意识到
了转瞬即逝的战机,准备与我一同进击,或是赴死!
然而,我们还是动不了。
因为,师母不放人。
因为,那泰山派的另一位娄长老,与那刚刚才从调息之中强行站起的秦天雷,
早已先我们一步,发动了最后的冲锋!
「老娄!跟老子一起上!」秦天雷吐出一口淤血,将体内所有的雷霆真气,
都凝聚于右拳之上!
「为了盟主!」娄长老同样发出一声怒吼,将他那面刻有泰山图腾的巨大盾
牌,如同最坚固的、最不屈的磐石,狠狠地向着那啸天魔君,撞了过去!
啸天魔君一斧将那本已是身受重伤,也不想和他同归于尽的秦天雷,再次击
退!
又一斧,则狠狠地砍在了娄长老的盾牌之上,将他整个人,都如同钉子般,
死死地压在了那冰冷坚硬的玄冰地面之下!
冷月已经抬起手来。
她这是终于要出手了?
「以血研墨,落笔成书。」
一声清冷不带丝毫感情的、雌雄莫辨的音色,却突然在这战场之上,缓缓响
起。
冷月放下手,轻声笑了起来——那【埋骨】的同伴,终于是开口了。
只见另一个黑袍刺客,不知何时,已然出现在了战场的中央。
那人瘦削无比,全身都隐藏在极为贴身的黑纱长袍之下,一头及腰的黑色长
发,在风雪之中狂舞。
胸部平平无奇,看不出是男是女。
手中,正握着一支,由不知名的、散发着淡淡幽光的纯白色神兽骸骨所打造
的骨笔。
此人居然以那冰冷的、沾满了鲜血的玄冰为纸,以那不知是谁的、温热的鲜
血为墨,在战场中央,飞速地书写着什么。
当那符文最后一笔落下的瞬间,将一口充满了自己生命本源的精血,狠狠地
吐了上去!
「莫动。」
啸天魔君的巨大魔躯,猛地一僵!他的行动,竟真的变得迟缓了!
「弃防。」
又一口精血。
他正在疯狂外泄的护体魔气,竟真的如同被阳光融化的冰雪般,进一步迅速
地减弱了!
「你……你到底是谁?!」
魔君惊骇地问道。
那人一句话不说。
【埋骨】则像一个最懂得把握时机的商人般,隆重地环绕全场鞠了一躬,向
在场所有的武林同道,也是他所有的潜在客户们,介绍着他这位,全新的神秘同
伴。
「……诸位,容我介绍一下,想必你们也是头次见,」他那沙哑的声音,充
满了不加掩饰的得意,「……这位便是我销金楼,新晋的第三刺客——【天谴】。」
「……欢迎大家,多多找他下订单!他一个人,就可以轻松胜过那三个,已
经死在了南疆的【死局】哦~」
「当然,他也和我一样,不会收那马上就要死的,就连我们刺客都唾弃的魔
头的钱……」
他嘲讽完这最后一句,便准备冲上前去,亲手结果了这已是囊中之物的啸天
魔君!
不行,不能让这刺客抢先。
那颗英雄心让我猛地拔剑,临渊出鞘。
「魔头,受死!」
一声属于年轻王者的嘹亮嘶吼,轰然炸响!
喊出这一声的,却不是我。
我已经被冷月一把按在地上啃雪了。
一道身着白袍的身影,比我更快,也比他更快!
他一手持足以洞穿一切的霸王枪,一手持足以斩断一切的君子剑,如同一道
金色闪电,转瞬便出现在了啸天魔君面前!
「滚!」
啸天魔君咆哮一声,就要提斧格挡。
「澄儿!不可!」那被死死压在地上的娄长老,发出一声恨铁不成钢的怒吼。
但他终究还是用自己的盾牌,死死地钳住了那魔君即将要回防的巨斧!
啸天魔君只好将所能调集的魔气全部用来防御,但已经迟了!
在那魔头充满了杀意……与憾意的眼眸注视下,枪出如龙,剑出如虹!
七品前期,「武林少盟主」——宇文澄,一枪扎进了那被上官影一剑穿心的、
同一个伤口!
另一剑……
「噗嗤——!」
一颗带着无尽狂妄与不甘的、狰狞的头颅,冲天而起!
我怔怔地看着那道在尸山血海之中傲然而立的、不比我年长多少的身影。
我的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我居然还曾以为,他不过是个只会仗着自己父亲的威名,作威作福的废物纨
绔!
没想到,他的实力,竟然已达七品化境前期!
我没有资格鄙夷他。
他比我……强得太多。
「这孩子叫宇文澄。你敢与他争这啸天魔君的人头吗?」
冷月师母那平静的声音,缓缓地在我耳边响起。
她看着那道年轻气盛、不可一世的最终「英雄」,闪过了一丝极其复杂、我
读不懂的情绪。
那里面,有赞许,有欣赏,也有一丝……隐藏得极深的担忧。
我收回临渊。
我扭过头去。
我不愿意承认,那冷漠得不像是烟儿母亲的宗师,是对的。
可她,确实是对的。
这一天,我学到很多。
太多了。
天山之上的第五战,就这样胜了。
可是,和我半文钱关系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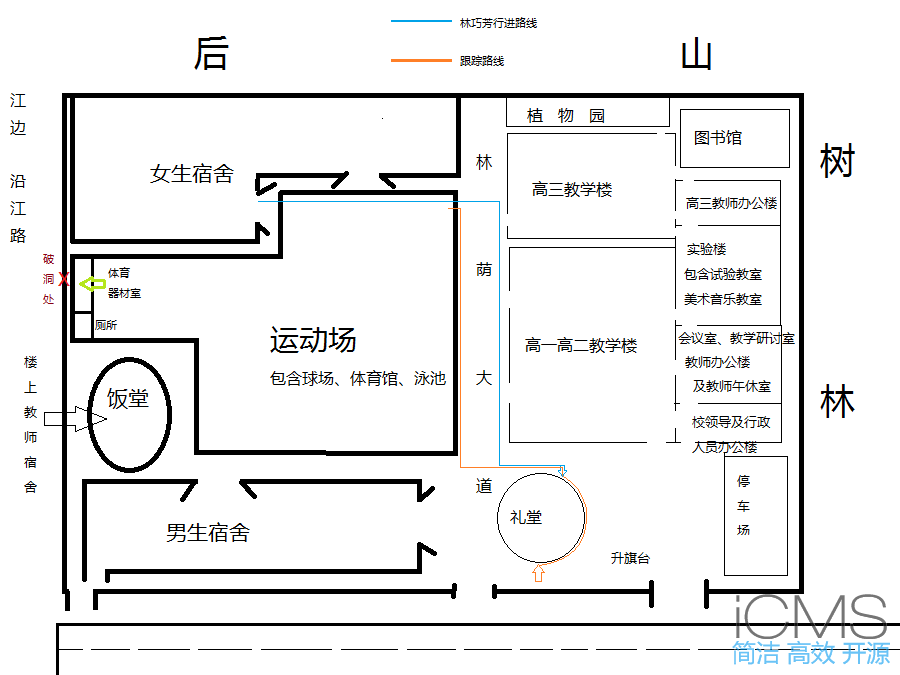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